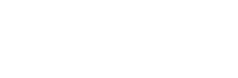老爹的两条钢筋腿已经软得像面条,从病床到厕所,才十来米的路,硬走了五分钟。
老爹的肿瘤原发于肝脏,一年前动了刀,但癌细胞喜欢开拓,五脏六腑都吃了它的败仗。
老爹跑了一辈子的船,江水里谋稻粱,老娘跟定他,洗衣做饭,把船屋收拾得清爽干净。病了也就一年多,船上早都乱得没处下脚,到处塞着中药罐子,船尾的药渣堆了一箩筐,各处木头缝里都熏进了药味。为了犟牛一样的男人,老娘跑断了腿,西医、中医、神医,都试了一遍。
老爹病情加重,老娘连续陪了几个大夜,快撑不住了,艾霞让她回去休息,自己顶上。
艾霞属狗,82年生在了船上。那时候,老爹只是长江航道上一个普通的沙工,追求老娘,只靠一副铁打的身板。两人在船上办酒结婚,孩子也生在了船上。老娘勤快,老爹肯苦,艾霞也乖,一家三口很快就拥有了一艘百吨级的小型沙船。老爹当了船老大,老娘当了船娘,艾霞的收获更大,童年世界里长江成了她的游乐场。
跑船28年,老爹的船升级成了千吨船,船变大了,他那副钢铁身躯却垮了。艾霞也28岁了,女儿7岁,大号双眼皮,樱桃小红嘴,骨相柔美,嗓门很大,哭和笑的声量都很惊人。娘俩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,就是肤色相差极大,艾霞黑皮黑骨,典型的水上人,女儿随爹,肤白面净,怎么都晒不黑。
艾霞的老公起先只是船上干活的沙工,肩头宽厚,出工不惜力,父母双亡。老爹老娘识他做上门女婿,艾霞瞅他也不反感,两人便按水上的习俗,走了婚礼的过场。结婚7年,女儿7岁,老公的优点还在,却多了一个没法容忍、且逐渐恶化的缺点:好赌;这当然也是水上男人共同的特点。
艾霞扶稳老爹,到了马桶旁,老爹一只手撑住扶手,另一只手握成拳头,在墙面上“砰砰”地捣了两拳。
“我要跟家豪一样年轻,这只铁拳就能把瘤子捣得稀碎,把家豪揍得满地找牙。霞啊,爹瞎了眼,没给你找个抵实(靠谱)的人。”
家豪就是艾霞的老公,比她小一岁,这两年日子过好了,赌博的瘾头也大了。前些年他手头的活干完,只去赌桌上争个百把块的输赢。近两年他变了,变成了真正的赌鬼,没心思干活了,跑去上新河的赌场里厮杀,整宿不回。
上新河是长江的一条汊河,河岸上到处是“销金窟”,吃喝嫖赌的生意搞得相当红火。跑船的人结了账,都去那儿消费。
艾霞跟他吵,先前闷葫芦一样个人,脾气见长,对着艾霞拳捣脚踹。老丈人体格还行的时候,收拾了他两趟,现在身体垮了,只任他无法无天。
“不晓得家豪是不是被人带去,当猪杀了,输掉一百万,这船指定保不住了。”
老娘立刻说,你赶紧带他回来吧,答应过他的,最后的一点时间,让他在船上过。
重新回到船屋,老爹的嘴角一整夜都挂着微笑,浑浊的眼珠子始终睁着,保持着一缕微光,盯紧了江上的天空,仿佛那里头藏着什么只有他能看到的东西——遥远、辽阔、谁都不能捉摸。
夕阳从水面浮出,渔网撒向水面,沙船出航的时刻,他终于闭上了眼,带着那抹微笑,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老爹一走,老娘一滴泪都掉不下来。她拧着眉头,跑前跑后,忙着办后事。兴许忙碌,才是对她最好的安慰,在忙碌中,对一位相处了几十年的枕边人,仁至义尽,划上情感的句号。
艾霞把老爹的骨灰撒进了长江,老娘引燃一张张冥币,江风卷起这些带着火光的碎片,仿佛江面出现了很多亡魂,伸出千百双看不见的手来争抢。
跑船的人不怕晒,江上的日头就像烤灯,把人晒得焦黑,跑船人也高兴。遇见雨水风浪,跑船人就得吃瘪,谁让财神爷跟太阳老爷是搭子呢。
艾霞的肤色就像抹了一层锅底灰,她不让女儿上船,总跟人说,江上的日头会把小女孩的骨头晒黑,将来女大十八变的时候,添皮添肉了,就长歪了,变成个小土妞。
一到暑假,老娘却总把外孙女往船上带,幸好小家伙的皮肉随她爸,禁得住晒。那个赌鬼臭男人,总算给亲骨肉留下了一点点优良基因。
艾霞想让女儿过上好日子,她一直待在船上,不晓得日子怎样算得上好。不过,船只要开进了黄浦江,她看见东方明珠,看见高楼大厦,常常幻想,那些扎在云端发亮的窗格子里都住些什么人,还有那些白皙洋气的大城市姑娘,她瞥见了,脸皮子就容易发烫,就想着一定要让女儿也住进那些窗格子,也这么洋气。
艾霞就有了一个很天真的理想,江面永远都是晴天,太阳越大越好。她只图每天能跑船出活,太阳老爷把她变成非洲人,也不带怕的。只要钱袋子鼓了,钱就是润滑油,船跑得顺风顺水,女儿的教育也能溜滑运转,将来就不用风吹日晒,就能过上好日子。
老爹走后,船舵和保险柜的钥匙都交给了她,她成了这条千吨轮的主人,长江航道上为数不多的女性船老大。
老爹那一辈的跑船人胆子肥,没有图纸,没有船台,也没有银行贷款,几个沙工四处借钱,到镇上的店铺买角钢、焊条,全都赊账,又去铁匠铺定制锚和螺旋桨,再跑长途,去山东的柴油机厂买设备,然后端着焊枪亲自上阵,就造出来一艘百吨级的货船。小船没有保险,风浪里闯荡了十多年,眼下总算换成了千吨级的大船,成了沙运航道里的“正规军”。
上海滩的沙子一吨卖40块,除外成本,一吨沙运回来能赚15块,一千吨沙就赚一万五,一个航次来回15天,一个月能赚3万块。水上的交易都走现款,船上的保险柜尺寸不大,稍不留心,就塞得满满当当,每次都是艾霞用报纸包好,匆忙上岸,找就近的银行存上。江面常有江匪出没,剪径劫财的事情不少。
江水里的好日脚走了没几年,老爹就患癌,赛钢赛铁的体格一下就垮了,老公又欠下巨额赌债,躲债躲得没人影,老丈人的葬礼都没敢露脸。
艾霞虽掌了舵,但她晓得,船恐怕保不住了,讨债的人就像一群蹲守的秃鹰,老船主一走,立刻就要来啃钢吃铁。这艘大船,一颗螺丝钉都剩不下来。
这天,水面下夜快,艾霞吃完晚饭刚放下碗,江面就像一团墨了。船上忽然停电,她以为是电机烧坏了,打亮电筒,去机仓查修,背后传来男人的咳嗽声,船上的狗又没叫,她以为是家豪。
江上的匪徒厉害,个个都吃淌血的狠饭。艾霞想,狗肯定没了。她不敢吱声,乖乖照办。
她赶紧往船屋跑,电筒也不敢开,夜色实在黑得可怕,她没走两步,额头就撞在了房门上。
老爹走后,船工都散了,老娘这些年又一直待在岸上照顾外孙女,船上就只有艾霞一个女人。
“哥,你缓我一阵,我跑船赚一笔,就还你一笔,多大的窟窿,我都给他填上,一点不给你损失。”
“哥,我是掏心肝跟你下保证了,你要丢就丢吧,我离了这船,我也没法活了。”
艾霞站着的时候,双腿打抖,这一躺倒,胆子也好像摊平了,面积变大,死都不怕。
“跟你好声好气,你偏要激我。你晓不晓得,我现在收债糊口,以前我可是江鹰,别逼我动刀子。”
90年代,水上的治安还是一片大盲区,脑筋活络的江匪就冒充沙工,在船上干个把月的活儿,摸清楚了保险柜的位置,就杀人抢劫,此类劫匪就是江鹰。
“活着我不能让船没了。哥,你动手吧,我老爹走了,我男人跑了,你帮我解脱吧!”
男人往后退了几步,点了根烟,火光照亮了他的侧脸,瞬间又暗了。艾霞瞅见男人的眼角有一道疤,蛮骇人。
“你每个月结了沙款,把钱用塑封袋子装好,弄一条青鱼,把钱塞鱼肚子里,船泊进老河口后,夜里你鸣三声笛,把鱼挂船尾,人不要过来,我来取。”
艾霞不晓得在地上躺了多久,泪水来得后知后觉,但势头凶猛,把眼角烫得发红。
跑船还债,艾霞转眼就跑了9年,37岁了,每天守着鸽子笼一般的驾驶舱,双手不离船舵,陪着太阳老爷红着脸出江,又红着脸下江。
她最喜欢夏天的傍晚,等船泊进了吃沙位,排队装沙要捱到天色漆黑,趁着云霞万丈的时刻,她就下水游泳,游出去老远。她认得不远处的一座孤岛,岛上长满了晒不蔫的野草野花,哪怕到了冬季,也有一些不知名的植物从冰霜暴雪里冒尖。她就一直游去岛上,把衣裳脱光,赤条条地躺着,让每一寸皮肤都吸纳地气。
老爹生前总说,跑船人水气大,缺地气。稍有空当,他总带着艾霞,去岸上走路踩泥。他总对艾霞说,土克水,跑船人要多踩泥,身上的运势才能平衡。
女儿16岁了,刚中考完,考得一般,勉强够上了二类高中。暑假被姥姥带上船,头发总算染成了黑色,平常不是绿的就是黄的。乡镇的中学管得松,学生们一个个都叛逆得不行。
女儿一上船,艾霞就带她登岛,吸纳地气。前几年,女儿很乖,就是挑食,不吃青菜,偶尔便秘。娘俩刚往地上一躺,她就来了便意,蹲到草丛里,放炮似的,劈里啪啦,一阵蹿稀。
“糯米在岸上生的,也在岸上长的,哪里需要吸纳什么地气。你就听你死鬼老爹的怪话,从来只把老娘的话当作耳旁风。糯米肠胃娇气,到船上了,让你做菜少放辣,我跟你讲过一百遍了,你哪回记得。”
“我说不让她上船,你又说我只顾跑船,孩子不跟我亲。水上日头这么紧,就算寒假过来,上岸也是晒得漆黑。”
老娘嘴硬,每次都说以后你别想见到糯米,一到寒暑假,照旧把外孙女往船上推。老人家害怕哪天身体不行,带不动外孙女了,她又不跟娘亲,将来如何是好。
这两年寒暑假,糯米的个头蹿得厉害,每回上船,艾霞都是眼睛一亮。她是典型的江南女子体型,瘦小玲珑。女儿大了,完全随爹,就连表情和走路的姿态都跟那个赌博鬼一模一样,脾气也同样差劲,表面上不吭不响,背地里不晓得捣鼓什么歪名堂,浑身上下,长了八百块反骨。
这几年,糯米越来越不乖,上船了只跟狗亲。她16岁了,高出艾霞一个头,艾霞再没听她喊过娘,叫谁都是“哎”的一声。今年中考,暑假放得早,等成绩出来了,姥姥才带她上船。头两天,她脖子上始终挂着一副耳机,甩着一张臭脸,艾霞想跟她讲讲话,她立刻就把耳机带上,听着摇滚乐,摇头晃脑地走开。艾霞憋了两天的火,实在憋不住了,就问她中考考成这逼样,还要上船当菩萨吗。
“讨债鬼,是不是当娘的也欠了你一百万。还有半个月我就过37岁生日,你一张好脸都不给我,是不是要气死我!”
艾霞给了她一个耳刮子,当天夜里她就吵着要下船,可头一天搬上船的东西实在多得不像话,电吉他、电子鼓、平板电脑……各种古里八怪的物件,还有许多让艾霞叫不出名字的游戏装备。
“每年两次的家长会,你们谁来过?孩子这次能考上高中,已经很好了,你什么时候管过孩子成绩?还跟孩子动手!”
艾霞也难受,想哄,嘴巴又笨,最后答应,暑假不限制她玩手游,她才止住了哭声。
跑船还债的9年,艾霞每出一趟活,都要偷偷攒下几千块,钱都交给了老娘。老娘却是狗窝里留不住剩馍,全由着外孙女瞎折腾。
糯米喜欢摇滚,喜欢重金属,老太太就跟着她去买装备,屁颠屁颠的。糯米每天在家弹吉他、打鼓、狗叫,周边邻居都成了敌人,老太太护犊子,就叉着腰跟邻居们舌战。摇滚的瘾头好不容易下去了,糯米又痴迷了网游,老太太的钱袋子很快被掏空,家里多了一台911黑武士二代台式机,供菩萨似的供在客厅里。
未成年人玩网游管得紧,糯米就花钱租号玩,上网课时也在玩游戏,两只眼睛就像涂了胶水,黏在电脑屏幕上了。老太太后怕,照这种趋势,糯米打游戏兴许会把眼睛打瞎。一到暑假,老太太就连哄带骗,赶紧推她上船,远离那个黑武士。
艾霞听不懂女儿的网络暗语,愣了一会儿神,又把目光放回了辽阔的江面。江水很蓝,水面像绸缎一样丝滑。她换了低档,船速减慢,江风柔了,把人的面孔吹得。她双手脱了舵,跑去船尾,喊了一声,又赶紧跑回来,重新掌舵。
这天清早,艾霞请了两个沙工上船,要去上海滩购沙。沙工喝了早酒,刚登船就盯着驾驶舱旁的晾衣杆,几条卡通丁字裤挂在江风里晃。
沙工的流氓话被艾霞听见了,她瞪了两人一眼。这凶狠的眼神,把两人逼得后退好几步。
“来几天事了,你当娘的,晓得不晓得?!她自己也不讲,裤头不洗不晒,让她光腚呀?”
“谁买的?她自己从网上弄的,互联网互联网,也不晓得是一张多大的网,尽是些古里八怪的东西。”
这几年,江上虽然都是太平日子,到处建了水警的趸船,但这两个沙工又脏又臭,墙上开个洞,都要想一想是公是母,脑子里全是脏念头。姑娘这么大了,难免叫坏人惦记,她就在驾驶位下面藏了一把菜刀。
打小,她就害怕沙工。9岁那年,长江的枯水期异常漫长,沙船都搁浅了三个月,她也到沙船上过暑假。
一入夏,水上人的日子比较岸上人,又多了几个太阳。早晨八点刚过,每家每户的船上就像挂着一只大烤灯,酷热难耐,男人们都裸着上身,女人们也只穿一件宽大的背心,干活时弓下腰来欧博官网下载,奶头也被晒得漆黑。人们得更多,欲望也无需遮盖。
沙工们整天喝酒打牌,有一天,一个沙工发酒疯,把她抱起来又啃又亲,把她下面也抠得淌血。老爹看见后,一拳打落了沙工的牙。沙工回到村里后,在酒桌上到处散播,让谁家的小子将来都不要娶她,她已经是个二手货。老爹追到村里,举着菜刀,撵得沙工满村庄乱跑。
艾霞被毁了名声,在村里待不住了,学也不念了,一直待在了船上。老爹跑船发家了,为了不让她受委屈,才招了个上门女婿,料不想,是个赌博鬼。
这趟船跑得顺当,沙工也卖力,等给人家结了工钱,她又觉得是自己神经质,菜刀都在底下捂出锈了。
夜里,她把船泊进了老河口,去水上集市挑了一条大青鱼,把两万块钱用塑封袋装好,塞在鱼肚子里,挂在了船尾。
跑船人重信誉,赌债不还的人是少数,要么上岸了,一辈子不再淌江里的浑水,要么就被讨债的人取走性命。
9年下来,她连本带利还账超过了百万,再跑一趟船,赌鬼丈夫的债务就彻底清掉。不仅船保住了,她也彻底解放,以后的心思全部能放在女儿的身上。丈夫最好一辈子不露面了,再见面,她立刻撵他下船,扯离婚证去。在集市上买鱼时,她顺带着买了西瓜、猪头肉、一瓶烧酒。
糯米不领情,还凶了老太太。艾霞上火了,三步并两步,走到女儿跟前,一把夺走手机。手机都烫手了。
“还敢跟我拿劲!老娘今天就要好好查查,你这个手机里到底藏没藏,让你眼珠子都胶里头了!”
糯米不吭声,一把夺过手机,用鼻孔瞅着她,猛将她推开,两条竹杆腿像跑跳的羚羊,从船上一下就跳到了岸上。
老河口的夜又黑又大,好在不出二里地,就能望见镇上的灯火。那儿竖立着几排高楼层的小区,一半烂尾,一半被开发商忽悠,卖给了城里的炒房客,密密麻麻的窗洞里只亮了几盏火。
镇上有个网咖,灯箱上挂满了蜘蛛网,网咖门口摆了一张台球桌,几个油炸摊子正开火冒气,小镇的年轻人都聚在这里。
“你惹她干什么呀,她气性有多大,你晓不晓得呀?这么多年,你不管孩子,那一分钟,又要你瞎管什么……这黑天黑地的,她能往哪去呢?”
艾霞和老娘都是江水里混出来的女人,胆量大,风浪天里跑船,腰背也打得直直的,丝毫不会慌乱。眼下,老娘慌了阵脚,艾霞自己,心脏也突突地跳,预感很不好。
艾霞在心里嘀咕着,各种情绪也在身体里杂糅一团,既后悔教训了女儿,又害怕女儿在夜里出什么意外,最古怪的情绪,还是一股前所未有的陌生感。
“找孩子吧?将将有个小姑娘,白白瘦瘦的,坐我摊位上,埋了张面孔,哭呢。我问她是不是饿了,递她一根火腿肠,也不吃也不讲话,站起身就跑了。”
两人赶到林子里,找了一圈又一圈。娘俩都是扁平足,几圈找下来,脚缝里都磨出了水泡。
艾霞细心一想,不大对劲。糯米吃耳光的时候都没掉泪,怎么就跑油炸摊上哭呢。
糯米是8点27分从后门进入网咖的,她站在后排,看一个胖子吃鸡甩狙。胖子甩得不赖,她给他鼓掌,胖子要抽烟,她又赶紧给人家递火。两人有说有笑,胖子还给她买了饮料,把机位腾出来,让糯米登录了游戏账号。8点50分,糯米突然情绪失控,把鼠标摔到地上,胖子骂了一句,从口型上不难判断,骂了一声“”。糯米从后门跑到了炸串摊上,从监控画面里消失了。
胖子还在吃鸡,老太太先冲过去,对准他堆了好几层的后颈皮,狂扇了几个巴掌。
胖子打个激灵,转过身来,正想还手,看见是个老太,拳头改成了巴掌,一把将人推开。
“小伙子,不好意思,耽误你玩游戏。将将有个女孩子,瘦高个,在你机位上玩了一会儿,就摔了鼠标跑了。那是我女儿,正寻她呢。”
“我不认识她,她自己贴上来的,我只是好心,机位腾给她玩王者,玩了十来分钟,她太菜了,脾气也臭,就跟队友互骂。那个队友是荣耀段位的大神,开直播的,直播间几百号人呢,就在公屏上挂菜鸡。也不晓得直播间有什么人认识她,说她是福利姬,一些照片从主播账号上晒出来了。她情绪失控,就跑了。”
艾霞不晓得什么是福利姬,胖子就点开公屏区的一个链接,扒出几张照片。女儿穿着不同款式的洛丽塔风格内裤,站着、趴着、跪着,瘪平的腚翘得老高,白皙皮肤上显出清晰的血管,到处写满了骂娘的脏话。每张照片每句脏话,都是一把尖刀,捅她杀她,剜心割肉,把她当娘的命置于死地。
“糯米也是扁平足,走不得远路,这么长时间,她脚底心都不晓得出来几个泡,再走不出几步路了。我们再寻寻,肯定能寻到。”
“小而深为潭,大而深为渊,两山夹水叫涧,山水分界叫崖,一面临水叫滩,两面临水叫湾,人工开凿叫渠,自然形成叫溪,掀起小波,掀起大澜,溪水汇聚为河,大河相连叫江。水分千派,终流入海。”
艾霞晕沉沉的,躺船沿上,江上的夜空潮闷极了,乌云密布。将将她摸黑回了船上,抓起一瓶烧酒,怼得精光。酒精刺激头皮,太阳穴一跳一跳,经脉冲撞着脑壳,试图释放什么东西。脑袋要炸开了,她大声念起小时候的识水歌。
船家的孩子都识水,唯独糯米不会。艾霞怕她晒黑,怕她命苦,预产期还有个把月,就住到了医院旁边的小宾馆,一点早产的风险都不愿意担,就是唯恐糯米生在了船上。
跑船人带孩子不容易,艾霞当年就生在了船上,老娘抓家务也要抓孩子,时不常还得帮着老爹掌舵。艾霞小时候不乖,老娘带她辛苦,常常用一根手指戳进烧酒瓶里,沾了酒喂她,再闹腾的孩子也只能去醉梦里打滚。
艾霞的酒量是一斤脚稳,两斤不晃,三斤不倒。今天兴许被糯米伤透了心,糟心酒的劲道猛,一斤烧酒下肚,她眼睛都不清楚了。
夜晚闷热,太阳穴跳得更猛了,身体也潮了,她踉跄着,走进船屋,爬进床下。江面潮气大,床下长了霉菌,挂着蛛网,她在木缝里藏了一颗震蛋。跑船孤苦,心情糟透的时候,她就拿它取悦自己。
她把它用防水的塑封袋装好,跳进江里,一直游到那座孤岛上。生下糯米后,她宁愿来泥浆里打滚,也不愿搭理老公。
身体里的浪潮终于退去了,酒醒了多半,人也缓过来了。她又觉得羞耻,痛骂一声:骚货生了骚货!
重新回到船上,撂地上的手机一直在唱《月亮之上》。等她抓起来,看见几十个未接电话,刚要接听,手机掉电了。
她想,指定是老娘跑不动路了,又催她去寻糯米。老太太不懂法,报警寻人,要过48小时,指定在派出所碰了壁。但细想一下,她又预感不好。老太太脾气犟,就算脚走断了,也不会打几十个电话过来。
一道闪电劈头而下,两声炸雷迅猛有力,又刮来一片潮风,江面的暴雨说来就来,一江夜水瞬间变成了一锅激跳的沸水。
手机断了线,江夜又划过一道闪电,密集的雨点砸在船顶,吵得人耳膜鼓胀。艾霞跑到岸上,没头苍蝇似的,到处寻人,嘴里嘀咕着:糯米没事,糯米没事的……
老河口近两年开发旅游业,建了一座跨河大桥,叫红丰桥。兴许工人作业太马虎,桥面的漆刷得不均匀,像泼了猪血似的,瞅着不吉利。一到丰水期,跳桥轻生的人,果真就不少。
老太太寻到桥上的时候,糯米已经没了,只留下一副beats耳机。手机也带进了水里,兴许手机里有太多她不愿旁人看见的东西。
耳机是老太太买给她的,当时糯米缠她缠了几个月。老太太起初不晓得这洋名字的耳机有多贵,晓得了又后怕,一百吨的沙子才顶得上这二两重的耳机。老头子当年那艘百吨级的小船,风里来雨里去,跑一趟来回,正好够上这轻飘飘的塑料玩意儿。
老太太咬破嘴皮子,下决心要拿下这副耳机的时候,糯米忽然懂事了,只说今年一双AJ都不要了,还帮着老太太洗了一星期的碗筷。那是糯米最乖最开心的时候,老太太觉得耳机买得值,一万吨的沙子都换不来。
“糯米呀!糯米!别吓姥姥!你躲哪里了呀!你打游戏,姥姥保证不烦你了!姥姥给你买7双AJ,一个礼拜,每天都换鞋穿!”
行车过桥的人瞅见了她,以为老人家想不开,赶紧来劝。她的喉咙早都哑了,情绪也没法平复,人家就报警了。
警车开上桥时,电闪雷鸣,暴雨不巧来了。水警出船搜寻糯米,江风掀开一片大浪,船险些翻了,汹涌的水流就像一只会说话的巨兽,嘲笑他们,人命不过是地上的一道划线,它伸出舌头就能把所有人舔干抹净,还妄想从它的嘴巴里捞人救人?
艾霞寻上桥的时候,雨停了,江风却大了,把人脸吹得像一团揉皱了的纸。老太太丢了魂魄,水警也像一只只疲倦的落汤鸡。
艾霞问糯米呢,谁都不吭声。她对紧江空,唤了几声糯米,黎明之中只剩她自己嘶哑的回音。
次日,江上的日头又紧了。暴雨过后,水量一上来,水流变得湍急。江水从不会轻易交还一具尸体,隔了好多个酷暑天,日头把一切都晒垮的时候,糯米总算找到了。
江水把糯米那身漂亮的皮肉泡成了黑紫色,体格也泡发了两倍,眼皮子也被水泡肿了,怎么都合不上。水警让艾霞辨认尸体,她一眼都不敢看,嘴里苦得不行,干呕了一次,胆汁都冒了上来。
老太太的面孔早被泪水和鼻涕糊住了,她看见尸体肚脐上有一个香疤,那是糯米小时候高烧惊厥,久烧不退,她到处求医,医生也没能耐,她连夜将糯米送去龙神庙,和尚在小孩的肚脐眼上烫了一个香疤。天亮时,糯米终于退烧了。为这事,艾霞还跟她吵过,怪她迷信。
“是糯米……我的乖乖呀!你为什么要想不开呀!姥姥一千个依你,一万个顺你!你咋就不念姥姥的好!你挖走我的心,挖走我的肝呀!”
老太太哭吼着,伏在地上,一遍遍地捶打尸体。水警拽她起身,殡仪馆的人将尸体拉走时,老太太躺在了车轮前面,不让人带走她的糯米。
艾霞想拽走老娘,身上的骨头却是软的,一点力气都没了。她也想哭,就是哭不出来,看见女儿的尸体,反倒想呕。胃酸泛上来了,她又憋了劲往回咽。
上海人注意:先别去!这条爆火的马路临时交通管制,期间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→
苹果Vision Pro预购这一晚:很多人抢到了,代购加价1.4万,苹果却推迟发货了
影驰预告两款名人堂 GeForce RTX 4070 SUPER 显卡:320W TGP功耗
27999元 雷神黑武士Shark台式上新:i7-14700K+RTX 4090D
XREAL创始人徐驰:AR眼镜将在未来10年内逐渐替代手机成为元宇宙重要终端市场